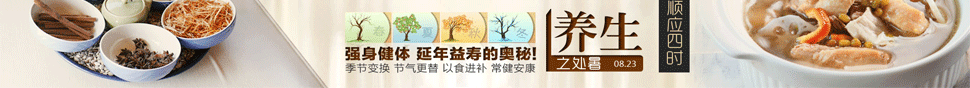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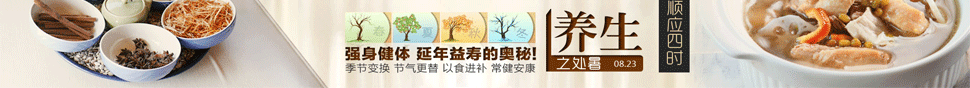
周京新,江苏省国画院院长、南京艺术学院美术学院院长、教授,硕士生、博士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画艺术委员会委员、江苏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江苏省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国国家画院特聘研究员、中国艺术研究院特聘美术创作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中国画作品获第六届全国美展银奖,第七届全国美展银奖,第八届全国美展优秀作品,第九届全国美展优秀作品奖,第十届全国美展铜奖。
年
在成就造型之前,型是谜底,是形;在成就造型之后,形是谜面,是型。
说到造型,往往就会拿似与不似之间说事儿,大家似乎都认同一点:画得太像就俗气,画得不像是骗人,而言下之意与画中所能则多趋向于有点像、不太像、大差不离的像就行了。于是,好端端的似与不似之间成了只能画得有点像或是根本画不像的“遮羞布”,莫名其妙地把宇宙飞船整成了幼儿手推车。在我看来,似与不似之间是一个关于如何超越像不像这个写实思维局限的造型命题,是要在画里集合神、态、意、趣、技等等绘画表现应该有的因素,构建起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特而完整的造型世界,像不像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而已。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相当艰难的工程,相当于在书法里创造一种书体。
年
独特是造型语言的筋骨,自然是语言品位的血脉。没有自己的筋骨,造型就有残疾,周身血脉不畅通,造型就会僵死。
年
那个暑假,我连续几天骑自行车去云龙山下的徐州博物馆看汉画像石,临画像石,体验和感觉汉画像石刻到笔墨写线的造型转身。两千多年前的画工刻匠们就有了自己实实在在的造型体系,至今依然展现着它那永恒的智慧、自信与从容。
年
我特别喜欢贯休、陈老莲,是因为他们的造型表现性如疾风骤雨般的强烈,造型风格独特而纯正,让我从中领略到构建绘画造型必须具备的章法品格和心境界。
传统经典向我们展示的主要价值不在于技术本身,而在于技术的生命原理。
年
贯休的造型突破了以往造型的种种惰性和狭隘,他把约定俗成的似从庭院统一盆栽一下子移植到了野逸险峻的山崖边,疾风骤雨中独自闲庭信步,龙吟虎啸前一曲高山流水,不温不火的东西霎时间变得骨相奇崛、鹤立鸡群,史无前例地超了凡,前无古人地脱了俗。一个个身形若顽石苍松那般刚烈的“贯休罗汉”赫然降世,以往那些似得温文尔雅的传神写照一下子都被陪衬成了“柔弱女子”。在传统中国画崇尚的各种似里面,“柔弱女子”太多太多,“贯休罗汉”太少太少,可谓阴盛阳衰。
年
敬畏老莲,但不悚老莲。
临其神采,感其体裁,悟其格制,觉我笔性。
年
人物眉目可以传神,举止动态也能传神。声色形态都是人体语言,各有其表露心境、传达情感的作用,一个手势可以传情,晃晃脑袋也可以示意,就连口、耳、鼻、舌、胳膊、大腿、脚丫子也都可以有情有意,从古到今的人物画造型与传神写照,从来就没有被传说中的“阿堵”眼珠子垄断过。
年
在民间画工那里,曾有过许多关于绘画造型的宝贵经验,例如,“画人难画手,画树难画柳,画花难画叶,画兽难画狗”,与《韩非子》里的“犬马最难……夫犬马人所知也,旦暮罄于前,不可类之,故难”的论点颇为相近。再如,“将无项,女无肩”“长舌鬼,高脚仙”等等。为了突出武将的魁梧,脖子不能画长;为了显示美女的窈窕,肩膀不宜画宽;鬼怪垂舌数尺,神仙高脚入云。从历代庙堂、洞窟、墓室的雕塑、壁画,到民间皮影、门神、年画、泥塑等的生动造型里面,都可以找出这些理论的实际依据。
简疏的线与繁密的线都是造型血脉,简不可跑风漏气,繁不能冗赘堆砌。疏可走马,密也能走马,造型才有活气。
我始终觉得,苦涩的造型历练比甜美的造型趣味更有定力,更有后劲儿。
对我来说,不觉苦尽甘来比一味甜甜蜜蜜要更加实在,更加自然,更加余味无穷。我的造型根基就在这里。
年
人物造型“开脸”最重要,在人物面部确立绘画图式元素,是构建造型语言最关键的核心步骤。“开脸”若搞出了名堂,人物造型语言就有了展开、深入、提升的基础,造型语言就能出彩,所谓举一反三。
年
“水墨雕塑”语言意在直觉现实物象,遵循传统绘画写意笔墨精神,借鉴西方雕塑语言体质空间与面性塑造形质。以笔为刀,既写既塑;墨应肌质,笔无常型;虚型实写,简象繁形。“水墨雕塑”的造型原理为:将约定俗成的先框架后填空模式,改造为一次浇铸成型体制。即将高度程式化的点、线、皴、厾、染等传统语言零部件统统融解化一,让先立骨架后敷皮肉式的“线写型”笔墨,升华为骨肉筋血皮毛同运同生的“塑写型”笔墨。在写意精神的自由释放中,“水墨雕塑”彻底摆脱了传统笔墨的“恋线癖”和“恐面症”,在给一直被误解和冷落的所谓“没骨”正名的同时,从笔墨身上彻底清除了零部件套版组装的烙印,让笔墨语言真正焕发“一笔画”的生命力。
年
心中有形,堪为得“竹”,心中有写形,堪为得“成竹”。既得“竹”者,可于浅小池塘涉水,嬉戏而已,并无惊险。“成竹”在胸者,则可入江河湖海踏浪,若鲸鲨自由纵横,击流壮阔,大作为也。自古以来,得“竹”者云云哉,得“成竹”者了了矣。
造型要真,真现形质,更显心境。真应该生长融汇在绘画语言的骨肉血脉里,而不是在表皮上张扬。
从整体到局部或是从局部到整体其实不仅仅是观察方法,更是具体构建造型的策略和过程。在创作过程中,无论整体的判断还是局部的经营,都必须从构建完整造型语言的目标出发,必须首先确立坚定、开放、灵变的构建语言意识。否则,过程可能永远只是过程,呈现不出有价值的结果。
年
戏剧人物是我内心挥之不去的乡愁,都市人物是我眼前必然面对的现实。一熟一生、一远一近、一旧一新的两个错落、交织、碰撞、融合的造型情节,在我心里和手上拉锯、切割、分合、取舍,构建着我的“水墨雕塑”语言。
画中造型生成我法者为上,仅得造化之表者为中,徒拟别人之法者为下,胡抹乱涂不觉者为零。
年
笔墨写意须造型通透,技意占全。技短意长,是有气无力;技长意短,是有力无气;技意俱短,是无力无气;技意俱长,是有力有气。有力有气而能交合造型者,气通力透,可入畅神之境。造而优则成型,写而化则生意,型入写则格净,意致觉则超然。
水墨写意的过程和结果应该是自由、自如、自在的,此前的生活体验、品位觉悟、个性定位、造型修为等等积累若是明确、完备而通透的,就能在创作过程中生成超然的自信与定力,进入自由、自如、自在的境界。
年
一如既往地创作会消耗造型积累中鲜活的东西,使它们日渐疲惫,养成惰性习惯,在逐渐趋于程式化的同时失去生气和活力。写生是一种极好的造型修养方式,与现实形象交流互动,在多吸取一些“生”的东西的同时,注意清洗掉造型习惯里的那些过“熟”的东西,使造型不断焕发生气和活力。
年
手稿就是创作。
不仅要追求画面完整,更要追求造型语言生动。
对我来说,每画一幅手稿,就经历了一次完整的创作与积累过程。
造型是一个虚虚实实的东西,往往要在有和无之间随机转换,从无处画出有,从有处画出无。有往往是实的东西,是“它”;无则往往是虚的东西,是“我”。
我的手稿从来都不是创作草图,而是一次次完整的创作体验,一幅手稿画完,就是完成了一次创作。
年
从不会画到会画,再到不会画,是几个质量完全不同的境界。手上的过程可以有备有略,心里的过程却是无法颠倒的。
有些手稿不是一次完成,过一段时间,甚至时隔数年,看着不满意,或是手痒了,拿过来又接着画,过瘾了为止。
在这样的“二度创作”、“三度创作”甚至“四度创作”中,我可以窥见自己的笔意变化,时过境迁,手上的感觉浓了还是淡了,厚了还是薄了,进步了还是退步了。
年
小小的手稿是一面镜子,令我自觉、自省、自勉、自立。
我的手稿是我思考、体验、感悟的“基地”,
我的语言之翼从这里养育、造就、起飞。
那些过“熟”的东西,使造型不断焕发生气和活力。
创作难免有心烦意乱的时候,
每到这时,手稿就是最好的“解药”。
年
我对学生强调“写”,是要让他们懂得中国画语言表现的核心技术精神是来自书法的书写性。
我一向禁止学生像我,一向鼓励他们去找自己的感觉,走自己的路。我一直相信,用心、勤奋是必须协调一致的两条腿,勤于思辨,勤于动手,就有希望找到自己,走出自己的路。
做老师这么多年,我做到了对任何学生都不放弃,因为我认为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潜质,无论是灵活的还是迟钝的,来得快的或是来得慢的,只要开发得好,都可能画出来。如果开发不好,灵活的、来得快的和迟钝的、来得慢的都可能画不出来。
手稿的积累是一张一张刻意坚持下来的,手稿的作用是一点一点无意显现出来的。我的手稿从来都不负我。
年
年9月初,我带学生去贵州写生,黔东南、黔西南跑了一圈,有时就住在苗寨吊脚楼里,晚上没有电灯,楼下就是猪圈,但我收获特别大,更难忘这段经历。
苗女着装的条块面体形态与我的语言构建理想暗合,助力我突出陈式,步入新境。
我的“水墨雕塑”语言构建就此呈现生机。
看苗家热热闹闹地迎客酒、拦路肉、跳芦笙、对山歌……
年
我满脑子都是笔墨造型构建:我要摆脱勾细线填墨色的禁锢,我的笔墨造型要自由自在地写开来!
苗家服饰造型节奏感很强,点线面、黑白灰与装饰纹样浑然交织,虚实结构明快,形神灵动一体。
当时我正纠结于写意人物笔墨构建瓶颈:程式的要转向现实的,别人的要变成自我的,单线型的要生成自由写性的……在这儿找到抓手了!
年
写生能修养观察方法,能修养语言品质,更能修养感悟意识。但是这些都不可能是现成的东西,不可能随手可得,需要主动地思思量量、寻寻觅觅、求求索索。
人物写生难于过模特儿这一关,心里被模特儿抑制住了,手上就发挥不开。要过这一关,先要解决受制于模特儿的被动局面,努力让造型表现意识当家作主。
人物写生未必一定要从眼面部起笔,既然这里麻烦最大,尽可以换个地方下手,如耳朵、肩膀、胳肢窝……心里的笔墨造型整体感觉,往往需要一个预热的过程,不妨先找麻烦少的地方下手,给自己一点时间。古人“或自臂起,或从足先”的做法也许不是为了炫耀本领,随机应变而已。
对模特儿的观察要很在意,但在意的不是纠缠于五官容貌、高矮胖瘦、服装款式等等的准确记录,而是在意如何把笔墨造型表现注入其中,让写生在落笔之前就有鲜活的表现意识。观察的目的就在这里。
肌理是造型语言的一把双刃剑,用得适度,能增强语言表现的亲和力;用得过了头,会显得刻意造作且累赘多余。无论如何巧妙精致的肌理,若是爬满了画面,都只会削弱造型表现的特质。花里胡哨的皮囊里面没有骨头,是造型缺钙语言低能的表现。
年
傣家女的造型不宜写实,拉直了,切方了,上短下长了,才西双版纳。
构图有点像张三,造型有点像李四,勾线有点像王五,设色有点像赵六……这样的“创作”是自虐,是对创作的玷污。在教学中,我宁愿鼓励学生摔自己的跟头,也不希望他们学别人走路。
应该鼓励学生在画里有想法、有追求,但画里的东西无论怎样都起码要达到比较“安定团结”的程度,就是画里的各种造型元素能够比较和谐抱团儿,不能是脏乱差一盘散沙的程度,否则再怎么样有想法、有追求都是空的。尽管我往往不甘心只要求学生的画达到比较“安定团结”的程度,但是遇到高不成低不就的情况,还必须这样要求。
年
我经常在创作课上对学生讲:大稿子过关了,你就可以回家睡大觉了!是想让学生在大稿子的打磨过程中,把造型的问题尽量处理到位,尽量不给下面的制作留隐患和遗憾。不过平时,我是不主张学生打稿子的,尤其在水墨写生的时候,不允许学生用炭笔、铅笔、木碳条等硬笔打稿子,那是希望学生能够摆脱稿子的依赖,尽快从先入为主的硬笔模式阴影里解放出来,激活直接运用毛笔去造型、去写意、去表现的感受力和控制力。
年
画彝族《看集》系列令我对雕塑感有了更加切实的领悟,淋漓的水墨与凝重的雕塑融合,中国画写意表现空间得以阔展伸张。
彝家人一扎堆儿,就是一组群雕,好似有了包浆的青铜铸就,活生生地伫立着。
课堂人物写生的时候,学生常常会“出师不利”,一开始就在人物面部遇到麻烦,出现各种造型方面的问题,于是信心受挫,阵脚被打乱,画不下去,或是“破罐子破摔”草草了事。按理说人物面部内容丰富,变化又多,应该更容易出效果,但在人物面部栽跟头的事儿岂止发生在学生身上。我想,这里的原因很简单,人物造型尤其是人物面部并非特别复杂难搞,而是一个特别深入人心的东西,在我们的心里特别真切、特别固定、特别不容篡改。于是,在这样一个特别计较逼真的朴素造型观的重压之下,心里越不想出错,手上就越容易出错。因此,我才在写生教学中特别注意对学生强调造型不等于逼真的道理,特别注重鼓励学生不怕出错、追求完整写生过程的完整体验。拘谨地坚持僵硬的标准,即便没有什么大错,也不益提倡;完整地追求表现的尝试,哪怕出了一些差错,也值得肯定。
年
我希望学生在课间的表现能够多种多样,因为他们的感觉原本就是多种多样的。但教学是有标准的,多种多样并不等于不要标准。而标准的灵魂就是品味,品味一旦出问题,高低优劣不分,就只能制造多种多样的低和劣。所以在教学中,我在鼓励学生注意“找自己”同时,总是特别注意引导学生修正、确立和提高自己的品味。
少数民族人物题材养育了我的水墨写意语言,回首这段经历,我依然心怀感恩。
圆珠笔的油泥劲儿好似饱墨中锋行笔,拖泥带水,润润苍苍,很给力的。
年
我觉得,苗家服饰有那么一种油油腻腻、纠纠结结、曲曲折折、碎碎叨叨的质感,然而若以“应物象形”为据,倒似很可以变通一番,另谋生路的。其实,传统经典都是十分厚道的,无论遇到什么情况,总是既规矩森严,又网开一面。
任何一种工具都可以在追求语言感的过程中焕发出超越其本身形质特点的造型意趣。
从普普通通的圆珠笔里我体验到了流畅、生涩、柔软、坚硬、松快、厚实、装饰、错落等等造型意趣,与我心里的笔墨思绪多有异工同曲的暗合。
年
鼓励学生坚持到底和引导学生灵活转移同等重要。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遇到各种瓶颈是常有的事儿,只要路子是对的,坚持下去就有效果,这时候老师有责任鼓励学生坚定信心,坚持到底。但如果路子不对,就应该及时调整转移,另辟蹊径才能走出困境,这时候老师则有责任引导学生反省自己的感觉,调整方向,灵活变化。无论是鼓励学生坚持到底,还是引导学生灵活转换,都要求老师能够真正做到因材施教,不以自己的好恶强加于学生,真正能够设身处地为学生着想,不误判、不误导学生。
我总是鼓励学生每张作业都要坚持画完,就是要克服各种半途而废的念头,坚持画进去,画到感觉的尽头,让自己在每张作业里都能完整彻底地体验自我感觉的得失利弊,进而不断总结经验,不断修正感觉,不断有收获、有提高、有进步。
十分便利的圆珠笔虽然只能画出线,却能妥妥地将线堆叠起来,构造线型之外的面型结构。每当我操着圆珠硬笔胸怀水墨写意的时候,都会有一种“身在曹营心在汉”的穿越激情。
我从来都不想把我的造型养成乖宝宝,我总是情不自禁地要在造型里面惹些事端,才觉得过瘾。倒是朴朴实实、简简单单的圆珠笔帮了我不少忙,谢谢圆珠笔!
年
中国画各课程教学必须强调线造型表现,学生能够比较到位地把线搞到造型里面去,才有本钱向造型要笔墨,进而向笔墨要造型。
水墨人物写生课上,学生往往会纠结于是“写实”还是“变形”,搞了“写实”的,往往会丢了笔墨;搞了“变形”的,往往就丢了造型。这样的尴尬纠结缘于陈旧刻板的造型观:造型=画得像。它极大地误导和破坏了学生对造型的理解、想象、把握和表现,必须在教学过程中坚决予以铲除,从学生的基本认识上加以修正。所以,我在教学中一贯强调:造型是艺术表现,造型≠画得像。“写实”只是造型表现的一个类别,且具有十分宽厚的可塑空间。“变形”不是胡来,也是造型表现,同样具有十分宽厚的可塑性,并非与“写实”对立。造型要有“造”,要有“型”,更要实实在在的有我!
年
造型如何才算好?舒服就好。合情就能舒服,所以合情比合理更重要。合情不一定合理,合理则离不开合情。既合情又合理也许挺好,但合情合理的造型切忌不冷不热、不温不火。
高考前我批评女儿速写画得不行,女儿不服,要求我现场示范一个……还是有些压力。
写意人物写生课程前期不宜对学术过多倡导轻松自由,因为那时候学生多是心里没底、手上拘谨的状态,所以要引导他们不过多计较笔墨的轻松自由效果,而是从造型结构出发,分析感觉造型,研究组织结构,先收后放,由紧而松,逐步确立认识,树立信心,建立方法。
我经常要求学生画得慢一些,不要匆匆忙忙像赶场子似的,心态平静专注了,感觉才有头绪;心里明白有数了,笔下才能淡定。“画得慢一些”不仅指运笔的速度,主要是指认识、思考、判断、理解、腹稿、笔感等等研究过程。中国画水墨写意运笔多有“草草”快捷之便,特别容易养成的潦草空泛的江湖浮躁习气,所以起步的时候就必须养成稳健入定的学术研究心态,有了这样的优质心态,以后的路就好走了。
年
课程与课程、课题与课题、作业与作业之间的街接要通畅,也要灵活变化。既要有实实在在的联系,也要有宽宽松松的余地。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既有明确目标,也有发挥的空间。写生可以直面实景分析并演绎其造型表现价值,更可以实际修炼笔墨在写实境遇中随机交合而不易写性根本的品质。写实与笔墨从来就不是敌人。
实景写生与闭门创作的状态完全不同,前者更多的是要清理取舍眼前的东西,后者则更多的是要经营把握心里的东西,前者如交新友,后者似会故人。
年
学生勇于探索是好事儿,要毫不犹豫地鼓励。但任何探索都要有道理,不能离谱,不能胡来。尤其当学生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基本跟着别人走的时候,要及时提醒他们以对自己负责任的态度去探索,去研究,那样才会有价值。
教学如同量体裁衣,每一位学生的体型身姿都不一样,必须因人而异。至于怎么量体裁衣,主要应该鼓励学生自力更生,老师的责任是帮助学生分析,提出合理建议,提供有益参照,引导学生“量”准自己的“体”,“裁”制出适合自己的“衣”。
教学中有许许多多看似顺理成章其实大相径庭的过程。如拟小草稿与上大稿子,落墨完毕与着色之后,写生训练与正式创作,创作过半与完稿之后等等,往往是前后效果迥然不同,多数是前面还好行,后门不行,虎头蛇尾。这说明学生对开始的预期与过程把控不对应,判断能力、制作能力和应变能力衔接不到位,且各有不足。这更说明教学中过程的完整体验及综合训练特别重要,一个方面、一个阶段、一个感觉的表现即便不错,也是不能替代的。
手稿鲜活,是我自己对自己说的悄悄话,创作何尝不应该如此!
年
鼓励学生坚持练习书法非常必要,未必是要他们成为书法家,重要的是通过书法去理解笔墨造型,把“画”提升到“写”的境界,这是一条最纯正的路子。书法是一把开通中国画笔墨的金钥匙,笔墨造型的根基就在于对书法经典的理解和运用。
在教学过程中,我总是刻意引导学生将素描、速写、书法、篆刻、线描、临摹、写生、创作、笔墨、线条、工笔、写意等等各课程关键词在认识上联系起来,并鼓励他们力求在感觉、理解和实践上把这些关键词打通,形成互为生发、互为补益的关系。这当然很难,但必须引导学生去追求。分科教学其实是一种迫于无奈的手段,在教学过程中就应该注意消除那些因分科教学而可能产生的认识上的隔阂与盲区。
年
教学标准是一把双刃剑,既要形成必不可少的约束力,以体现高等院校专业教学的基本原则;又要注意避免对学生的潜质造成压制,破坏培养有艺术创造力人才的教育目标。教师是这把双刃剑的主要掌控者,要坚持讲原则,也要保持灵活性,宽严、松紧、收放之间须因人而异,因势利导,合理合情地处理与应对。
人物、山水、花鸟、写意、工笔,喜悦、郁闷、兴奋、无聊、清闲、忙碌……都不应该左右一个画家的创作状态。
一个好画家必须养成高质量的状态,高质量的状态应该通透开放,应该无所不至,应该随机应变,应该淡定超然。
当形式与内容没有了界限,画里的形式就是内容,内容就是形式的时候,绘画性的品质就纯粹了。
年
中国画是一条比较狭窄的路,一届一届学生学出来的模样几乎大差不离,好像没有别的路可走;中国画是一条十分宽阔的路,从古到今总有一个个牛人标新立异,开天辟地。教学如果一味延续驾轻就熟的老套路,就只能是一条狭窄的路;教学如果能够真正将视野开放至精彩纷呈的古今中外历史经典,就一定是一条十分宽阔的路。
专业教学从来都是“当代”思维和“当代”行为,不要以为拿顾恺之、张彦远、宋徽宗说事儿就是回到了古代,根本没有过,我们只是在以“当代”的心境怀古而已。所以,在教学中强调“当代”性与强调“回归”古代都是无聊之举,正视眼前才是真实的。
让学生感觉到中国画经典的纯正品格是教学的首要目标。当然只有老师先搞明白了,然后教学生明白什么是中国画的高品质、高格调、高境界,教学才会有希望,才会有价值,否则,就是误人子弟。孔子云:“朝闻道,夕死可矣”,就是倡导这么一种誓不与庸碌见识为伍的悟道品德。
只教会学生染来染去的制作工艺,那是专业教学的悲哀。企图用染来染去的工艺制作取代笔墨表现,那是当代中国画的悲哀。
比较常规地品味,比较常规地借鉴,比较常规地积累,比较常规地画下去,是比较常规的路子。
常规的东西总是占多数,但历史告诉我们,往往非常规的东西才是变革、创新、发展的重要推手。
年
学校、教学、教师等等因素所形成的是一种比较纯粹、比较学术的研究氛围,真正积累、修养、发挥、把握学生艺术感觉的主动权在学生自己手里。艺术感觉往往隐藏在人的心灵深处,它往往很私密,很闪烁,很不易捕捉,像一个羞涩的精灵,需要殷勤养育、精心调理、准确激发、反复磨砺。对于这个羞涩的精灵来说,学校、教学、教师等等因素不应该是空调、交警、变电站,而应该是春夏秋冬、日月山川、风云雷电、阴晴雨雪……
学生学会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很重要,而学生学会用自己的手去做自己看到并感悟的更重要。
要求学生画得深入一些,并不只是要他们多画几笔,更不是要他们把画面画满了为止,而是要求画面的结构关系达到饱满而合理的程度,这不是量的问题,而是质的问题。少少许可能是比较深入的,多多许可能是不够深入的,画里的结构关系从来都不是以多少来衡量深入程度的。
年
视野开阔总比狭隘好,积累宽厚总比单薄好,广泛借鉴总比专工好,心境包容总比偏执好。
要鼓励学生多画速写,大量画速写能有效提高基本造型能力,把绘画手感提升到一个可以造就的程度上来。速写好似最普通、最廉价的盒饭,能够及时解决最基本的饥饿问题,快捷有效地提高学生的基本造型能力;速写也好似最昂贵、最神奇的真君手指,可以点石成金般地点化学生的艺术感觉,让睡着的灵感醒过来。
对待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出现的“毛病”,做老师的一定要有逆向判断意识,因为学生的一些“毛病”很可能是老师固定不变眼光判定的,是被“毛病”的,如果做老师的思路能够开阔一些,灵活一些,设身处地一些,学生的那些“毛病”就很可能是某些可以挖掘的个性潜质,“毛病”就很可能变成优点,变成能走出独特精彩的好路子。
年
对传统经典技术语言的学习和运用,重在不入俗流地品味,重在由量而质地感悟,重在举一反三地发挥。要求学生在短短的几年里练就石涛、八大那样的笔墨“功力”,是误人子弟行为,很多潜质不错的学生就是被这样的伪“功力”忽悠至残的。
写实真好,人人都喜欢。不过,我依然决意要在实之外更多地追求写,进而让写把实搞定、搞透,搞成一个整体、通透、灵变、超凡的活物。
学生画画的时候慢慢养成的好习惯今后就能够形成语言,形成个性风格,受用一辈子;而那些不好的习惯就会形成各种毛病,形成不良习气,自己把自己毁了都不明白。好习惯最关键的是品味向经典靠拢,认定阳春白雪;不好的习惯最致命的则是品味向末流靠拢,与低劣媚俗为伍。
年
写生可以有效医治学生心里没谱、手头生疏、眼力迟钝、散乱无章等毛病。静物、模特和实景里面有许许多多鲜活的东西,能让学生直接体验到没有被修饰、篡改、污染过的生态活气。写生需要基本技术方法支撑,具体技术方法须因课程而异,但必须有高起点,必须要求学生从适宜本课程效法的各类经典技术方法中选择借鉴,借用最牢靠的梯子,去采摘最新鲜的苹果。
我非常反对学生直接把速写放大成“创作”,这样特别容易把速写里的求便利、求速成、求简单、求快捷等等速写性的东西直接搬到画里来。速写这样求便利、求速成、求简单、求快捷没错儿,那是它的长处和特点。中国画则不同,笔墨造型都有自己的讲究,广泛吸收借鉴的前提是保持本色,任何时候都不能舍本逐末。所以,我经常地、不断地、明确地告诫学生们:再好的广场舞也成不了芭蕾!
年
画里各样东西的主次关系是可以自由转换的,只要整体关系自然顺畅了,小的可以是主,大的可以是次;淡的可以是主,浓的可以是次;虚的可以是主,实的可以是次。
插图的线、连环画的线、速写的线、工笔画的线与线描课要求的线是不同的,前者的各种线是合唱、合奏、群舞里的若干分之一员,后者则是独唱、独奏、独舞,不是群武群殴,而是单打独斗。
年
由不清楚到清楚再到不必太清楚,是教学的常态线路,学生的认识,手上的感觉,线条的把握……都会经历这样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针对学生的状况,教学引导和要求应该调准角度,及时变换。学生还搞不清楚的时候,要把他们往清楚上引导,追求纯正地领悟;学生想要什么都清清楚楚,钻牛角尖的时候,则要把他们往不必太清楚上疏导,讲求智慧地变通。
人物线描写生课程不应该对线条的质量过多要求,而要特别强调整体造型和结构关系,训练学生以单线编织形象、表现意趣的能力。一堆毛线不能当衣服穿在身上,只有编织成了毛衣才能穿上身。从毛线到编织针法,再到毛衣的款式,就是线描写生造型从局部到整体的结构关系,搞定了这些关系,毛线、针法、款式才能各自体现出自己的价值。
手稿具有开发想象力的功效,
想象力是不需要说明的。
年
我最注重的还是造型表现本身。具体说来,就是首先要创建出完全属于我自己的画中型格,“型”是样式,“格”是品位。样式不是自己独有的“型”,再好也没有用;品位够不上传统经典的“格”,有什么样式也白搭。
素描、速写是中国画造型语言研究非常得力的帮手,多种多样的素描、速写能够多样化地帮助多种多样的造型观察、构思、创建和定位。我一直认为,只要造型语言研究的立场准确坚定,就让素描、速写这样的帮手喧宾夺主,即使是被一位画家前辈斥为“有害无益”的契斯恰科夫体系的素描、速写,也能给中国画造型语言研究提供某种有价值的启发和参照。盲目否定有借鉴价值的台阶,上路登高要么是一件单调且枯燥的事儿,要么是一件困苦而无助的事儿。
当创作构思草图遇到速写造型练习的时候,造型先喝出了:哥俩好!
二手联成一手,合成了一门实实在在的造型创作练习功课,益莫大焉!
年
造型是绘画语言的主心骨,有了这个主心骨,绘画语言就能天马行空;没有这个主心骨,绘画语言就是行尸走肉。其实早在魏晋之前,中国民间绘画就已经很有造型这个主心骨,天马行空者大有人在。宋元以后,传统中国画因书法之写性在画里的势力越来越大,工笔重彩向水墨写意自然转换,期间就有书写性造型觉醒的重要作用,中国画语言写性笔墨造型表现的时代就此开启。
无论想要怎么去画,关键在于如何找到属于自己的造型语言,并将它有声有色、自然而然地表现在画里。造型应该是一支真正的“兵符令箭”,只要能把它弄到手,就可以调动你想要调动的任何一支军队。那些手里没有这支“兵符令箭”,却莫名其妙地大唱“空城计”的门外汉们,其实是误会了自己手里的那根“鸡毛”,且永远都领略不到“我正在城楼观山景”的超然境界。
手稿功课能锻炼造型,但搞得不好也会在造型里养成毛病和习气,所以我会时常提醒自己:做功课要举一反三,在小幅线形的图稿里思考笔墨,养育笔墨,构建笔墨。
写实从来就不是写意的敌人,两者往往似歌词与歌曲的关系,其完美的融合,才有艺术表现的完美。
年
我的“水墨雕塑”有两个出发点:一是语言尚写性,笔墨当道;二是造型做加法,深入塑造。把水墨和雕塑这两个看似不相干的东西弄在一起,就是要搞一出风马牛的“拉郎配”,使笔墨写意造型表现出塑造丰富空间关系的潜质,让塑造呈现写意性,让笔墨具有雕塑感。
中国画造型从来都没有排斥过写实,从来都是主张要追求似的。一千多年前的唐代张彦远先生写的中国第一部绘画通史著作《历代名画记》里面就已经讲得非常明确:“夫象物必在于形似”,画画首先就要做到形似。不过,传统中国画的形似是一种特别讲究骨气、立意的写实,是一种超越简单模拟逼真的写意之似,是一种追求“以形写神”绘画表现的、超级版本的像。那些将一般的像强加于中国画,或者将一般的不像栽赃给中国画的做法,都是不入门的东西。造型准不准,只是绘画一个方面的标准,相当于看一个国家粮食产量高不高;造型有没有艺术表现性,则是绘画本质方面的标准,相当于看一个国家是不是文明富强。
我的手稿不是那种快捷记录的“速写”,而是一张张即兴完成的小型画作。
我从来没有把手稿当成创作草图,或另行放大加工制作成大画,因为我觉得它们已经是完整的作品了。
画面的所有背景都是可以好好利用的,不要仅把它们当作陪衬的东西应付了事,对它们同样要倾注笔墨造型关照,没有笔墨造型盲区的画面才是完整的画面。
人物活性,姿形种种,不可拘于动静,意写天象,神韵可得。若正似屏展,勿失错落;侧若墙脊,须显递转;蹲如屯鼎,当呈夯势;坐比瘫棚,需现墩态。
年
画面中造型之外的各种空白,所谓“负形”,其实都与造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都应该成为造型表现的一个部分,虚实相生讲究的就是眼里光有实不行,也要有虚;要让实里生出虚;虚里长出实;实可以变为虚”,虚可以转成实。一旦虚与实形成了灵活自由的互为依托、互为转换、互为生发的格局,造型表现的空间和效果就能够更加灵便,更加通透,更加出彩。
造型在被笔墨感化的时候,必须保持住自己的定力;笔墨在被造型牵引的同时,也必须展现出自己的品行。笔墨与造型只有相得益彰且融为一体,才能完美组合并体现其和而不同的价值,也才能就此体现出中国画写意语言的高度。造型笔墨化,笔墨造型化,是中国画必须面对的头号难题,不明白这个难题,中国画就是个门外汉;曲解了这个难题,中国画就是个山寨货;不屑于这个难题,中国画就会去中国画。
画画靠的就是感觉,心里的感觉,眼里的感觉,手上的感觉都要到位且通透一气,才是好的感觉。好的感觉是要养护的,堂堂正正、实实在在地做人就是最好的养护。
一边画速写一边看电视是很惬意的事儿,只是不能经常这样惬意,上瘾事儿小,养成勾来勾去的习气就麻烦了。
人物造型有三关,头一关:将形画化。第二关:将画我化。第三关:将我真化。过得此三关,可有好前景,过不得三关者,半途而废。
把生活与想象捆在一起,一切都可以变得随意灵活:不可能的变得可能,不相干的变得相干,寻常的变得不寻常,死掉的变得活过来。
年
由光造成的明暗,是造型可以很好利用的元素。在画里面,光和明暗可以各种面目出现:聚起的,分散的;紧贴着的,松弛着的;从外向里的,从里向外的;合情合理写实的,无中生有写意的等等。造型语言在这方面施展开了,光和明暗就有了多种多样的用武之地,画的路子也由此而豁然。
画中之法,造型二字可以全概。造型之道首先是造,凡图、形、笔、墨、色等诸项,都应该造就成型。从一笔一墨之小,到画里画外之大,或先有各小后成大一,或先立大一后治各小,但求小形入得大形,大形造成大型;小与大形通神透,大与小格法合一。至于造得的型,则无论先后大小,皆须品行兼备。品者,好骨,好韵,好相,好格;行者,可伏,可起,可入,可出。变,则换形不易其象,守,则化一不损其格。如是者,型致矣。
速写是一种不能间断太久的长期投入,回收到的效益应该是保持良好的状态和敏锐的感觉。
造型是画里的顶梁柱,非同小可。它可大可小,可粗可细;可方可圆,可曲或直;可虚可实,可放可收;形式多样,变化无穷。
但无论如何,造型必须有一定的模样。造型的过程和方法则必须收放结合,情理并至。
若对它规矩过头,它就会变得小里小气,撑不起架势;若对它全无整制,它又会变得没轻没重,立不住根基。
有形处以型造笔,无形处以笔造型。
年
人物造型是绘画语言元素的第一世界,其他任何系列元素都无法比拟。对人物造型的认识上了档次,就会有不俗的语言作为;人物造型语言有了不俗的作为,搞定其他题材就不在话下。
似与不似之间是一种非常高明的造型观,是一种既确定又灵活的造型感觉和艺术状态。然而一旦试图建构一个与它相关的、新的造型表现空间时,难度是很大的,因为,似与不似之间绝不是大差不离、可有可无、模棱两可,而是要求你在似与不似之间这么一个很宽很阔的造型领域里找到自己的落脚点,并有无愧于似与不似之间经典造型观的造型作为。
以细线练习人物造型,心思要在造型上,不能困在细线里面,因为中国画造型虽然讲究线,但不等于线,尤其不等于细线。
造型被规定为线型框架结构,被轮廓化,是对绘画语言的一大制约。在这一极度程式化的轮廓化框架之内,造型的骨、肉、皮、毛等被一一精工细作,打造成同样极度程式化的填充物,终究是套件组装、骨肉分离的格局。
年
无论古人画人,还是今人画人;无论画古人,还是画今人,都离不开传神,造型不传神,或是传得不够神,就不配为造型。然而,传神有时是一个陷阱:为了把神传到位,很容易钻到喜怒哀乐的情绪故事里去,忽略了造型本身应该有的讲究,不够格的造型里传出来的神,肯定也是不够格的。传神有时是一块“遮羞布”:在造型这种硬件上无所作为,就试图利用传神这种软件走捷径,在以空洞苍白的玄虚大肆忽悠的同时,掩盖造型硬件的低能与平庸。
线是一把塑刀,切出来的形是线,挖出来的形是点,剐出来的形是皴,削出来的形是面。
造型关系是绘画创作中最有价值的关系,也是最有利可图的关系。充分利用好这一丰富多彩的关系,可以获得许多提升画面整体效果的机会,诸如笔与造型的关系、墨与造型的关系、色彩与造型的关系、透视与造型的关系、情节意趣与造型的关系、局部或整体各结构与造型的关系等等。
年
造型如果能够将画面空白和“负形”部分也一一鼓动起来,各自融入造型的节奏中,整体呈现出以虚应实、计白当黑的格局,所谓气韵生动才有实现的可能。
造型当然需要刻意经营,否则难以构建。真正有价值的随心所欲、顺其自然其实是立意高明、不露痕迹的刻意经营,与稀里糊涂地碰运气根本不是一个档次的事儿。人物面部内容特别多,所以特别难画,但也最能有造型效果,也最值得先有造型效果,因为它是构建造型语言的“领头羊”。
造型写意化,是绘画语言至高级别的表现,造型像与不像、精准与否,则是绘画技术低级别的门槛儿。用高品位的意引领造型,以高格调的写主导表现,造型才能成为可以登堂入室的语言。
记录一个场景,影像更强;叙述一个故事,文学更强;表现一个旋律,音乐更强;塑造一个形象,雕塑更强。绘画能做的其实就是绘画本身。
线与面之间从来没有截然的界限,它们可以彼此依托、交织、转换。对它们的任何限定与分割都是在自寻狭路。
中国画造型的玄机在于深刻领悟书法精神,并在技术上生成为一种超越勾勾、描描、点点、染染,使“形似”“骨气”“立意”“用笔”通透贯一的实际修为,将书法用笔的精气神移植到画里去,让畅意灵动的书写性注入到造型骨子里。这样,造型才有可能摆脱那些工艺性制作的拖累,升华为品格高洁、张弛有度、自由自在的表现语言。
年
造型求“深入”,并不是多画几笔就能解决的,而是要在造型结构关系上做加法,不是量的增加,乃是质的提升。古人所谓“下笔便有凹凸之形”者,其实就是把握造型结构的一种超凡修为,那是一种以一当十、步步为营的战略,与蜂拥而至的人海战术不可同日而语。
造型要真,真现形质,更显心境。真应该生长融会在绘画语言的骨肉血脉里,而不是在表皮上张扬。
速写能快捷记录,能积累素材,能锻炼造型,能提高创作能力,也能把一个画家尤其是“中国画家”毁成一袋“方便面”。
初试写生,如果能做到有笔有墨,还能画得像,那是最好的。如果暂时不能兼顾,可以把墨先放一放,首先解决笔和像的问题,就是先尽力让用笔的地方都有造型,或者是追求造型全用笔来表现。但必须明白,像只是造型的一般属性,其程度上的调节余地是很大的,若一味追求逼真,拘泥于所谓的像,笔就难以生存。至于笔本身,则当以呈现写性为要,不可仅以线条为是,线条只是笔的某一类形态,且在线型上亦有许许多多的转换空间,将线与笔画等号,是短见低能的表现。眼睛只盯着像,造型就只能赚得立锥之地而已;将视角由单一的线,开放至无限的笔,造型就可以有海阔天空的自由。
造型是一个虚虚实实的东西,往往要在有和无之间随机转换,从无处画出有,从有处画出无。有往往是实的东西,是“它”;无则往往是虚的东西,是“我”。
中国画讲究用线,但从来没有规定细线才是线。在开放的空间关系中,线的粗细、长短、方圆、曲直、疏密、聚散等等形质都是可以自由转换进而无限变化的。
形与神血肉相连,不可分离。真得形,须两全,舍其一,则俱失。
形应笔造,笔运形生。应物形而蕴笔象,象笔型而意写。依自然造化之象,而得笔墨写意之天。
形似是中国传统绘画特有的书写性图型表现模式,是将物形升华至画型境界的写意语言核心元素。中国画讲求的所谓写意就是追求艺术地表现,写意表现需要心境与理法相互融通,灵动变幻,彼此彰显。
形之所以要与似捆绑,是因为似具有适应写意表现的品质,那就是造型的写实程度适中且自由,生动表现而不拘泥于肖似,从而给生性自由的笔墨语言留出切入写意性的空间。从心境理法到笔墨造型,只有彼此融合、通透一体了,才有价值和意义,才无愧于写意这一几千年铸就的中国画艺术经典。
手上的创作草图可以简而略之,心里的创作构想绝不能有盲点。
独特是造型语言的筋骨,自然是造型品位的血脉。没有筋骨,造型就有残疾,血脉不畅,造型就会僵死。
与万紫千红的大自然拼色彩是很不明智的,单纯而独特的水墨写意最能够体现一种不可替代性。
“水墨雕塑”是我在水墨写意造型语言方面的一种探索。“水墨雕塑”最初的动机就是要将传统中国画语言的框架结构变成整体浇铸结构。“水墨雕塑”遵从传统经典品格,借鉴中西雕塑艺术空间理念和表现原理,将写、雕、塑三者交融组合起来,构建起一个写骨塑韵、型雕质写,使造型呈现笔墨化,使笔墨具有雕塑感的崭新的写意表现语言。
年
写意里有意趣,有笔墨,有色彩,更有造型。造型是写意里无处不在的东西,是呈现艺术表现的主力。写意、笔墨、色彩往往因造型的活力而千姿百态、千型万种、千变万化。写意造型可粗可细,可屈可伸,可大可小,可疏可密,可疾可缓,可放可收。写意笔墨造型完全可以是“细笔”,而“粗笔”则不等于写意造型。“细笔”和“粗笔”各自也都可以呈现千姿百态、千型万种、千变万化的造型。而在细与粗之间,则依然有着千姿百态、千型万种、千变万化的无限造型的空间。
眼前的自然实景好似一台大戏,角色多样,景象流转,情节跌宕,好看的东西太多,写生的时候非得正儿八经地笔墨纸砚认真伺候一番,才对得住这般自然神奇的天地造化,仅用普通硬笔勾勾速写真是罪过!
中国画造型历来是有空间意识的,以平面的写来模拟立体的实,所求之似,乃是中国画造型语言特有的结构程度定位,是艺术表现的一种高明策略。因为,似能够回避实可能给写带来的种种制约和拖累,中国画的写意精神由此确立。
认为写意造型必须求简,简才是空灵的,才是最高境界,那是一个误区。倪云林很好,很简,很空灵。王叔明也很好,虽然很繁,也很空灵。其实画里的境界必须先在心里确立,心境高,画境就高;心里干净,画境就空灵。画面上的造型简也好,繁也罢,都必须是心境的真切表露,而不能是一副遮丑的面具。
我特别不情愿对景速写,仅以硬笔单线做做简单记录,很不过瘾,好似要我扯根柳枝去编一顶皇冠,很无奈地大题小做。
年
画里的故事不需要有太多的小说式情节,绘画从来就不是文学的马仔。
线是造型结构的自由版程序,可以无限升级,也可以自由更新。线可以有出处,有中生有,举一反三;线更可以无出处,无中生有,自有我在。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米勒:苦难的生活与温情的画面
李老十:有些东西是与生俱来的
冯小刚以万拍下的素描版《圣山》
黑白涌动
VikiKollerová
曾翔
裸体手稿
罗丹、克里姆特和塞尚
全国政协委员卢禹舜:两会提案
巨匠“达·芬奇”:完美的人,是衡量宇宙的尺度
木心:世人只知道我的诗歌和绘画,却不知音乐才是我的命
自画像!并不是所有画家敢尝试的…
一个美国女人69年前敦煌朝圣,她拍下了我们不曾看到的敦煌
哈尔滨市青年画院青年画家常绍亮
哈尔滨市青年画院青年画家韩周一郎
哈尔滨市青年画院青年书法家黄晓蕊
哈尔滨市青年画院青年画家王艺霖
哈尔滨市青年画院青年画家沈鹏
哈尔滨市青年画院青年画家仲伟然
哈尔滨市青年画院青年画家李晓宇
哈尔滨市青年画院青年雕塑家鲁斌
哈尔滨市青年画院青年书法家常乐
哈尔滨市青年画院青年油画家张琨
哈尔滨市青年画院青年画家王晋
哈尔滨市青年画院青年画家陈英文
哈尔滨市青年画院青年书法家张志超
哈尔滨市青年画院青年画家丁春冬
哈尔滨市青年画院创作室主任研究员、青年油画家刘明宇
他选择骑自行车前往西藏,为心爱的“她”,为证明我“还活着”----记哈尔滨市青年画院副院长、青年油画家“梁彦达”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